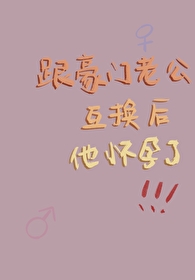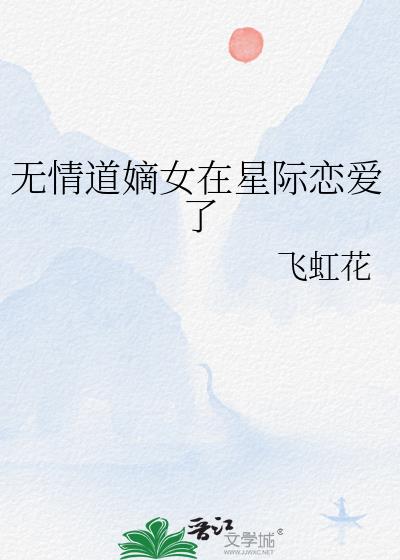青泥洼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柏奇小说beranm.net),接着再看更方便。
寺庙的播音器里播放着低沉缓慢的诵经声,三线香火光明灭,灰烬叠满八宝烟炉,成股的烟丝窜入鼻腔,模糊了整座大殿。
金身佛像低垂着双眼,悲悯地望着身前俯首跪拜喃喃自语的诚心人。
佛身后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鎏金牌位,在两侧蜡烛的火光中熠熠生辉。
牌位上那小小一寸人像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初生婴儿,年龄跨越近一个世纪,年纪大的不是没有照片,便是黑白或是发黄的旧照片,若是有彩色的,那么像中老人一脸皱纹,透露着活够了的麻木。有些夫妻同牌位的,妻子的照片还年轻而丈夫已经老迈,少见的有共白头的合照,眼中就带了点笑。
有些二十多年前便挂在这里的年轻人,照片已经发黄,但年轻的大多都是蓝底白底彩照,脸上多少挂上鲜活的气息,牌位前摆着瓜果泡面小零食,显然常被人挂念着。
钟嘉慧一眼就看见了罗芸,她不似往日笑得猖狂,只是嘴角轻轻浮现出微笑,眼角微弯,这在成千上百张已经算得上特殊,更何况她还那么漂亮。
在她身边,是一个叫夏花的女人,1966年生人,活了四十三岁,照片应当是三十来岁时拍的,漂亮得像画,只是眼角眉梢带着些惆怅,似乎是她那不长的寿命的征兆。
她的供奉人是她的儿子,黑色字迹有些模糊,钟嘉慧看了半天,才隐约分辨出来:
『阳世
儿
吴霖
拜荐』
钟嘉慧愣怔住了,她眨了眨眼睛,挥散眼前烟雾,才终于确认,这个名为夏花的女人,是她的婆婆。
吴霖从没同她提起过,她只知道他英年守寡的母亲在他大学毕业那一年死了。
罗芸嘴角弯弯在笑,夏花眉眼低垂像在哭,神像抬起下颌用温厚的嘴唇似笑非笑地俯视着她的心神不宁。
“小钟,”罗父恭敬地将线香插进香炉中,喊她,“该烧纸钱了。”
钟嘉慧又看了一眼罗芸。
少顷,她点燃三根线香,沉默地跪上蒲团,拜了三拜抬头,莲座上盘膝而坐的佛依旧慈眉敛目,仿佛她刚才的一瞥只是错觉,它依旧是宽恕众人的神佛。
她定了定神,慢慢将线香插进挨挨挤挤的香炉,就在插下瞬间,烧了半截的线香忽地一抖,带着火光的灰烬落上了她的手背。
罗芸拧人很有一套章法,她先是揪起一点点皮,紧接着用指甲使劲扭转,这种痛是直入神经骨髓的,这么多年以来,只有她在犯糊涂想要把外婆遗嘱里送给她的老房子送给她哥时才被拧过一次。
这烟灰燎人与罗芸拧人不相上下。
钟嘉慧沉默良久,轻声说:“对不起。”
罗芸笑得一点都不灿烂,含蓄地,甚至带着一点藐视地俯视着她,她不再与罗芸对视,转身向罗父走去。
罗父已经老了许多,几日不见,他头发全然变白了,他只有罗芸这一个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一边把薄薄的纸钱丢进焚烧炉里,热浪掀起灰烬飘向四周,空气中微小的草木灰无孔不入地刺激着周围人的眼睛,没一会钟嘉慧眼里就泛起泪花。
“西山太远了。”罗父突然说,“这里离家更近,我就把罗芸带到这里来了,最近事情太忙了,就忘记告诉你了,很抱歉。”
“…没事。”
人最先出现老态的是长相,接着是身体,最后才是声音,罗父声音苍老而无奈:“这样就算等年纪大了,也能随时随地的过去看望她。小钟,你是罗芸玩得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了她…等我走了,也有人能记得她。”
钟嘉慧背后不自觉的渗出细密的汗珠,整个人就像被绵密而潮湿的水汽包裹着,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但于此同时她的喉咙干得冒烟,就像是沙漠上几天几夜未曾饮入一滴水的羁旅之人,她咽了一口唾沫,顷刻间化为蒸汽。
“好…”她干涩地挤出一个字。
罗父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异常,他丢进最后一张纸钱,把捆扎的草绳团成一团丢进去,又说:“我们把罗芸的东西收拾了一下,那些乐谱之类的东西,我们也看不懂,你要是看懂了,能不能让我们也听听?”
钟嘉慧点头。
罗父的声音里就带上了笑意:“你阿姨行动不便,我就没让她过来,她叫我买了你喜欢吃的鸡翅,让你今天中午去我们家吃饭,中午留下来吧。”
她不爱吃鸡翅,罗芸喜欢。
罗父是做小生意的,读的书不多,更别提蝌蚪一样的音符了,翻了几天罗芸的遗物,什么都看不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懂行的人过来就很高兴:“也不知道她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才会喝了那么多酒。”
钟嘉慧苦笑起来,她知道为什么,但她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也不敢和罗父的视线对上,低头小声说:“我去看看。”
*
罗芸的房间被收拾得很整洁,床铺被整理得一丝不苟,床头摆放了一个蓝白格子的长抱枕,柔软的被褥平整地铺